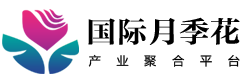全部商品分类



那一年我16岁,为了一株月季茶饭不思。
是初春一个微凉的午后,我排了长长的队伍,从老师的手中领养了它,并小心翼翼地将它植入教室门前的小花坛里。那时的我,因为卑微,无人关注,读书常常心不在焉,上课的时候,老师在前面讲优美的诗词,我却走神,想起黄昏里属于我的月季。春风悄无声息地漫进来,轻拂着我的短发,又随手翻乱了桌上的书本。我用力地想啊想,却还是不知道:究竟那一株瘦弱的月季,何时才能听见我的祈祷,从细细的枝杈里发出绿色的小芽来。
没有人知道我的焦虑,事实上,我如那株枯萎的月季一样,被人忘记了。不管疼痛与喜悦,浓烈还是浅淡,都不会有人去注意沿墙低头走路的我。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忽略,假若偶尔有人大声地在班里提及我的名字,我反而会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兽,有想要瞬间消失掉的恐慌。大部分的时光,我缩在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的座位上,将老师们的声音当成背景,而后任由自己的思绪在天空蓝色的幕布上自由地飞翔。这是我在别人的张扬里最为安全的存在方式,一如那株在繁花似锦的春天里从来没有蜂蝶流连过的月季。
那一小片花坛,植了30株月季,我的那一株始终无声无息,没有任何舒枝展叶的痕迹。负责浇花的园丁说,这株月季定是枯了,否则为何外面吵嚷一片,它却固执地缩在泥土里不言不语?但我还是百般地恳求那个好脾气的师傅,无论如何都不要忘了在施肥浇水的时候,多多眷顾这株孤独的月季。
这样的乞求并没有奏效,园丁在一株株欣然吐叶的月季面前,每每还是将它忘记,或者即便是视线飘过,也不作短暂的停留。这是一个花团锦簇的春天,空气里弥漫着湿漉漉的芳香,浓郁,热烈,常常就有女孩子的尖叫锐利地划破傍晚的寂静,她们彼此开心地叫嚷着,自己的月季又长出了一片叶子,抽出了一条新枝。那新鲜的小芽,竟犹如婴儿的双唇,是可爱柔软的红色呢!我蹲在花坛边上,看着那株干裂寂寞的月季,听着别的女孩子兴奋又夸张的叫声,还有操场上隐约传来的篮球撞击水泥地面的响声,终于将头深深地埋进臂弯里去,哭了。

春天不过是一个转身,便走掉了。校园的红砖路上,青草在一次次踩踏里弯了又直直了又弯,蔷薇越过墙壁开出袅娜的花朵,藤蔓缠绕着爬上高高的梧桐,初夏的风翻转着层层密实的枝叶。而我的月季,它在我日日的守候里,依然选择了沉默。
花坛里的月季已经竞相地开放,最好的一株长在靠近我那一棵的左侧,枝叶蓬生开来,将那一方小小的角落全都遮掩住了。园丁师傅许多次都以妨碍观瞻的理由要拔掉我的月季,却每每都在我的苦苦哀求里住了手。他不明白,总是问我:“丫头,这不过是一株发到你的手中便已经奄奄一息的花而已,何必如此较真儿地守护着它?”而我,总是倔强冷硬地只有一句话:“它不只是一株月季。”
是的,它不只是一株月季,它是16岁的我,所有的期待、梦想与童话。我固执地认定,假若它真的不会醒来,那么,我的青春也会如它一样暮气沉沉,了无希望。
那个闪亮的童话,就在盛夏的一个清晨苏醒过来。我守护了整整一个春天外加一个初夏的月季,终于从泥土中生出一片卑微但却执著向上的新芽。那株枯萎的枝杈,依然安静地挺立着,等待那柔弱的生命,一天天向上,向上,直至最后,远远超越了它的高度……
我的月季,在温暖的泥土里,蛰伏了整个的春天,错过了争奇斗艳的季节,却还是来得及在阵阵蝉鸣的盛夏,一点点地靠近馥郁的花香。
16岁的那年夏天,我的每一本书里都飘散着月季的芬芳。我将第一朵花凋零时的花瓣,全都细心地收藏进书本。它们的红色深深浅浅地嵌入温情的文字中,每一次读,都能嗅得到它最初绽放时饱满恣意的芳香。
而这样的香气,从16岁时那个自卑的丫头,一直缭绕到而今自信从容的我,历久弥香,再也不能让我忘记。